即时焦点:——潮汕英歌舞题材美术作品前的凝望
有些文化,是从土地里跳出来的,一点点,一代代。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英歌舞就是这样。它是一种节奏,藏在身体里,养在街巷间。
有人跳着它长大,也有人,把它画了下来。
1994年刘启本画下《遍地英雄——潮汕英歌舞印象》,那是一幅带有时代印记的版画,用简练的黑、红、黄构成激烈节奏,在今天看来依然真切、沉着,充满清醒的判断力。他没有着力描绘人物的细节面容,而是以群像式构图和步调一致的肢体姿态,勾勒出一股从地面腾起的力量感。
那时还没有“文化自信”的提法,但那份信念,已经沉在画里。没有聚光灯,也没有口号与鼓噪。只有刀锋深深浅浅,画面沉静,分量却十足。
当时英歌舞还不是一个被艺术表现聚焦的题材。画家只是刻下了自己熟悉的生活节奏,那是田埂上走路的步伐,是乡村节日的鼓点,是一群人默契而踏实的动作。他没有刻“非遗”,也没有刻“英雄”,只是一刀一刀刻出那种集体之间的信任,那种落地有声的气质。黑色打底,红与黄交错,画中没有激昂的口号,却像有一股从地底撑起的力道。那不是为了谁而“燃”,而是一种静默中的信念,像土地深处缓缓涌出的热流。
正是这种真挚,悄悄地影响了后来许多画家。他们看见了那些刻进木板的面孔,那些阳刚的身姿,不只是传统民俗的记录,而是一种英歌舞文化之美——沉默的、深植的、让人靠近也让人敬重的美。
后来画英歌的人逐渐多了起来。
卢中见的《潮汕英歌舞》,画的是另一种气质的英歌舞。在他笔下,不再是节庆的喧嚣,而像一场潮汕人自己的仪式。对称的队形、昂扬的动作、精致的脸谱,都有一种被提炼过的秩序感。他让英歌舞变得庄重,甚至带着肃穆的气息。画面不喧哗,却自有章法;情绪收敛,却更显克制。
他并非本地人,却在画布上小心翼翼地靠近潮汕文化的精神肌理。他画的,不只是“跳英歌”的动作,而是在揣摩潮汕人内心的规矩感。画面中没有追风逐浪的动势,反而更像是一次对“形”与“势”的信仰表达,是他眼中对潮汕文化“如何安顿自己”的理解。
他的作品更像是一种整理过的传统,以尊重的态度回望传统,并尝试以自己的方式重构其精神。他用一种自己的方式,去理解这片土地上的尊严与分寸,也以此回望,潮汕人如何在文化中建立自我认同的尺度。
冯少协的《潮汕英歌舞》则是另一种表现路径。他画的英歌,是燃烧的,是腾跃的。红、黑、金、黄等色块在画面中炸裂,腾空的人物仿佛把身体交给了鼓声,将信念一口气抛向空中。那不是简单的跳跃,而是将传统高高举起,也将当代的自信,一点点从身体、色彩与节奏中释放出来。这姿态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表达,一种从内心跃出的力量。
冯画的,不是“跳英歌”的人,而是“被英歌舞跳动”的人,画里不只是舞者在动,更像是情绪在舞,精神在舞。
画中的“燃”,既是喊出来的热血,也是默默记住的节奏;是服装上的红与金,更是潮汕人骨子里的步伐与气息。它就如英歌舞本身——外在热烈,内心沉着,这份热烈,是鼓点中跳出的自在,是一次次高抬腿后的坚定,也是生活中,人们眼底那道不动声色的光。
蔡拥华的《汕头开埠区》将英歌舞放进了城市的中心。他让英歌走近中山亭,走进小公园,亭下红衣鼓队,亭后欧式骑楼,街坊围观,人群涌动。他让英歌从庙口走上城市中心,让鼓队站进中山亭下,也让那份节日的精神,登上了更广阔的舞台。他画的,不仅是“英歌”,更是“汕头”——一种正在凝聚的城市性格与文化自信。
如今的英歌舞,已不仅是节日的热闹,更是这座城市内在节奏的文化象征。英歌舞正通过画布,走进更大的视野,也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认识潮汕的精神气质。
而在画布之外,更多年轻人正用镜头、脚步,甚至一段节奏感强烈的说唱,把英歌的步伐带入新的空间。他们用新的媒介继续“跳”,也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传统的创造性转身与文化的当代表达。
汕头经济特区走过四十五年,有速度,有奇迹,更有一种安静的坚持。这座城市靠一次次踏实的落地,一步步走出自己的节奏。
英歌舞正是这种节奏的象征。它在街头跳过,也在画布上站稳;它走出庙埕、走进都市,又从民族节日走向国家展厅,甚至走向世界。它不为取悦谁而表演,而是在表达一种无需翻译的情感——对土地的信任,对团结的倚靠,对未来挑战的默默迎上。
那些英歌舞的画面,不只是文化的图像,更像是一面镜子,映出潮汕的骨气,也映出潮汕的灵魂。一个把热烈藏在节奏里,把信念走进生活的地方。
这,便是潮汕的文化自信。
也是汕头继续前行的方式。
-
 即时焦点:——潮汕英歌舞题材美术作品前的凝望 有些文化,是从土地里跳出来的,一点点,一代代。英歌舞就是这样。它是
即时焦点:——潮汕英歌舞题材美术作品前的凝望 有些文化,是从土地里跳出来的,一点点,一代代。英歌舞就是这样。它是 -
 重点聚焦!龙湖区龙腾街道赴广州、厦门等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本报讯近日,龙湖区龙腾街道组织招商考察团赴广州市、厦门市、泉州市及
重点聚焦!龙湖区龙腾街道赴广州、厦门等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本报讯近日,龙湖区龙腾街道组织招商考察团赴广州市、厦门市、泉州市及 -
 世锦赛丨中国女排3:1胜哥伦比亚队 收获两连胜提前晋级16强 人民网北京8月26日电(记者胡雪蓉)北京时间8月25日晚,2025年女排世锦
世锦赛丨中国女排3:1胜哥伦比亚队 收获两连胜提前晋级16强 人民网北京8月26日电(记者胡雪蓉)北京时间8月25日晚,2025年女排世锦 -
 当前热议!图解财报:南极电商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362.07万元,同比减少82.52% 南极电商发布2025半年度报告显示,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3 53亿元,
当前热议!图解财报:南极电商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362.07万元,同比减少82.52% 南极电商发布2025半年度报告显示,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3 53亿元, -
 韩国购买100多架波音飞机 韩国购买100多架波音飞机,韩国,波音公司,大韩航空,波音飞机,知名企业,
韩国购买100多架波音飞机 韩国购买100多架波音飞机,韩国,波音公司,大韩航空,波音飞机,知名企业, -
 我国自主研制超大型耙吸挖泥船将下水 观察 经过3年多研制,今天(8月26日)中午,我国自主设计研发建造的两艘超大型
我国自主研制超大型耙吸挖泥船将下水 观察 经过3年多研制,今天(8月26日)中午,我国自主设计研发建造的两艘超大型
-
 黄金市场的波动对投资者心理的影响如何?-当前关注 黄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产品,其市场的波动会对投资者心理产生多方面的
黄金市场的波动对投资者心理的影响如何?-当前关注 黄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产品,其市场的波动会对投资者心理产生多方面的 -
 即时焦点:——潮汕英歌舞题材美术作品前的凝望 有些文化,是从土地里跳出来的,一点点,一代代。英歌舞就是这样。它是
即时焦点:——潮汕英歌舞题材美术作品前的凝望 有些文化,是从土地里跳出来的,一点点,一代代。英歌舞就是这样。它是 -
 “父婴室”火爆网络 为奶爸带娃提供育儿空间-新要闻 “父婴室”火爆网络为奶爸带娃提供育儿空间记者走访:南京部分商场育婴
“父婴室”火爆网络 为奶爸带娃提供育儿空间-新要闻 “父婴室”火爆网络为奶爸带娃提供育儿空间记者走访:南京部分商场育婴 -
 【速看料】比亚迪e5补贴后落地价多少比亚迪e5纯电动车多少钱 【比亚迪e5补贴后落地价多少比亚迪e5纯电动车多少钱】随着新能源汽车市
【速看料】比亚迪e5补贴后落地价多少比亚迪e5纯电动车多少钱 【比亚迪e5补贴后落地价多少比亚迪e5纯电动车多少钱】随着新能源汽车市 -
 中国宏桥(01378.HK)8月26日耗资5007.71万港元回购203.4万股|即时焦点 格隆汇8月27日丨中国宏桥(01378 HK)发布公告,2025年8月26日耗资5007 7
中国宏桥(01378.HK)8月26日耗资5007.71万港元回购203.4万股|即时焦点 格隆汇8月27日丨中国宏桥(01378 HK)发布公告,2025年8月26日耗资5007 7 -
 当前热讯:经纬线·国旗的尊严 由我们捍卫 一面国旗,他扛在肩上,用青春守护共和国荣光;一个动作,他千锤百炼,
当前热讯:经纬线·国旗的尊严 由我们捍卫 一面国旗,他扛在肩上,用青春守护共和国荣光;一个动作,他千锤百炼, -
 8月27日生意社石油焦基准价为2412.50元/吨 8月27日,生意社石油焦基准价为2412 50元 吨,与本月初(2390 00元 吨)
8月27日生意社石油焦基准价为2412.50元/吨 8月27日,生意社石油焦基准价为2412 50元 吨,与本月初(2390 00元 吨) -
 重点聚焦!龙湖区龙腾街道赴广州、厦门等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本报讯近日,龙湖区龙腾街道组织招商考察团赴广州市、厦门市、泉州市及
重点聚焦!龙湖区龙腾街道赴广州、厦门等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本报讯近日,龙湖区龙腾街道组织招商考察团赴广州市、厦门市、泉州市及 -
 Argus下调斯凯奇评级至“持有” 视点 ArgusResearch将斯凯奇的评级从“买入”下调至“持有”,目标价维持为6
Argus下调斯凯奇评级至“持有” 视点 ArgusResearch将斯凯奇的评级从“买入”下调至“持有”,目标价维持为6 -
 焦点快看:骑士官宣!前开拓者队视频协调员将担任附属球队剑客队主教练 骑士官宣!前开拓者队视频协调员将担任附属球队剑客队主教练,伊莱,nba,
焦点快看:骑士官宣!前开拓者队视频协调员将担任附属球队剑客队主教练 骑士官宣!前开拓者队视频协调员将担任附属球队剑客队主教练,伊莱,nba, -
 沪渝蓉高铁武宜段满足开通运营条件 武汉坐高铁1小时可到宜昌 8月26日,随着55402次试验列车从宜昌北站驶出,沪渝蓉高铁武汉至宜昌段
沪渝蓉高铁武宜段满足开通运营条件 武汉坐高铁1小时可到宜昌 8月26日,随着55402次试验列车从宜昌北站驶出,沪渝蓉高铁武汉至宜昌段 -
 2025年平板玻璃题材上市公司,这份名单别错过!(8月26日) 据南方财富网概念查询工具数据显示,相关平板玻璃题材上市公司:三峡新
2025年平板玻璃题材上市公司,这份名单别错过!(8月26日) 据南方财富网概念查询工具数据显示,相关平板玻璃题材上市公司:三峡新 -
 比轿车还省的十大省油SUV有谁 【比轿车还省的十大省油SUV有谁】在如今油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下,越来越
比轿车还省的十大省油SUV有谁 【比轿车还省的十大省油SUV有谁】在如今油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下,越来越 -
 光云科技:融资净买入198.41万元,融资余额1.58亿元(08-26) 2025年8月26日光云科技融资净买入198 41万元,融资余额1 58亿元
光云科技:融资净买入198.41万元,融资余额1.58亿元(08-26) 2025年8月26日光云科技融资净买入198 41万元,融资余额1 58亿元 -
 通讯!三亚这群消防员台风天彻夜奋战 8月26日,蔡扬驰(前)和队友在三亚河东路一小区内排涝。三亚传媒融媒体
通讯!三亚这群消防员台风天彻夜奋战 8月26日,蔡扬驰(前)和队友在三亚河东路一小区内排涝。三亚传媒融媒体 -
 光电子器件相关公司哪个好_2025第二季度毛利润排行榜 《南方财富网概念查询工具》财报工具数据整理,截至2025第二季度,光电
光电子器件相关公司哪个好_2025第二季度毛利润排行榜 《南方财富网概念查询工具》财报工具数据整理,截至2025第二季度,光电 -
 本田雅阁7代参数配置详解 【本田雅阁7代参数配置详解】作为本田雅阁系列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代车
本田雅阁7代参数配置详解 【本田雅阁7代参数配置详解】作为本田雅阁系列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代车 -
 焦点速递!记者:德科与马略卡高层会面,商讨福特等多名球员的未来 记者:德科与马略卡高层会面,商讨福特等多名球员的未来,德科,福特,巴
焦点速递!记者:德科与马略卡高层会面,商讨福特等多名球员的未来 记者:德科与马略卡高层会面,商讨福特等多名球员的未来,德科,福特,巴 -
 观点:[快讯]龙星科技503万限售股9月3日解禁 CFi CN讯:龙星科技(股票代码:002442)在2025年09月03日新增可售A股5
观点:[快讯]龙星科技503万限售股9月3日解禁 CFi CN讯:龙星科技(股票代码:002442)在2025年09月03日新增可售A股5 -
 AGV送货机器人龙头有这三家(2025/8/26) AGV送货机器人龙头有哪些?据南方财富网概念查询工具数据显示,AGV送货
AGV送货机器人龙头有这三家(2025/8/26) AGV送货机器人龙头有哪些?据南方财富网概念查询工具数据显示,AGV送货 -
 本田十代思域报价和参数是多少 【本田十代思域报价和参数是多少】作为一款备受消费者喜爱的紧凑型轿车
本田十代思域报价和参数是多少 【本田十代思域报价和参数是多少】作为一款备受消费者喜爱的紧凑型轿车 -
 热头条丨马卡:巴萨为注册球员,可能被迫出售卡萨多与费尔明 马卡:巴萨为注册球员,可能被迫出售卡萨多与费尔明,孔德,马卡,巴萨,卡
热头条丨马卡:巴萨为注册球员,可能被迫出售卡萨多与费尔明 马卡:巴萨为注册球员,可能被迫出售卡萨多与费尔明,孔德,马卡,巴萨,卡 -
 603359,重大资产重组!停牌!-独家焦点 603359,重大资产重组!停牌!
603359,重大资产重组!停牌!-独家焦点 603359,重大资产重组!停牌! -
 引江补汉工程“江汉领航号”TBM掘进始发-今日热文 湖北日报讯(记者彭磊、通讯员邱悦来、王应昆)8月25日,在宜昌市夷陵
引江补汉工程“江汉领航号”TBM掘进始发-今日热文 湖北日报讯(记者彭磊、通讯员邱悦来、王应昆)8月25日,在宜昌市夷陵 -
 奔驰为什么喜欢用仿皮奔驰仿皮和真皮的区别_焦点消息 【奔驰为什么喜欢用仿皮奔驰仿皮和真皮的区别】在汽车内饰材料的选择上
奔驰为什么喜欢用仿皮奔驰仿皮和真皮的区别_焦点消息 【奔驰为什么喜欢用仿皮奔驰仿皮和真皮的区别】在汽车内饰材料的选择上 -
 每日讯息!中国平安:截至上半年平安银行不良贷款率1.05%,较年初下降0.01个百分点 8月26日,中国平安发布2025中期业绩。2025年上半年,平安银行实现营业
每日讯息!中国平安:截至上半年平安银行不良贷款率1.05%,较年初下降0.01个百分点 8月26日,中国平安发布2025中期业绩。2025年上半年,平安银行实现营业 -
 《哪吒2》吃饱 光线传媒2025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增长近四倍 播报 报告期内,光线传媒营业收入为32 42亿元,同比增长143%;归属于上市公
《哪吒2》吃饱 光线传媒2025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增长近四倍 播报 报告期内,光线传媒营业收入为32 42亿元,同比增长143%;归属于上市公 -
 消息!工信部:截至7月末5G基站总数达459.8万个 【工信部:截至7月末5G基站总数达459 8万个】工信部发布2025年前7个月
消息!工信部:截至7月末5G基站总数达459.8万个 【工信部:截至7月末5G基站总数达459 8万个】工信部发布2025年前7个月 -
 观速讯丨重仓股名单浮现,这些公司二季度获券商增持 重仓股名单浮现,这些公司二季度获券商增持
观速讯丨重仓股名单浮现,这些公司二季度获券商增持 重仓股名单浮现,这些公司二季度获券商增持 -
 天保基建(000965.SZ):上半年净利润1.18亿元 同比增长2106.58% 格隆汇8月26日丨天保基建(000965 SZ)公布2025年半年度报告,上半年公司
天保基建(000965.SZ):上半年净利润1.18亿元 同比增长2106.58% 格隆汇8月26日丨天保基建(000965 SZ)公布2025年半年度报告,上半年公司 -
 医病更医心!“心身同治”助脑梗患者重获健康 今日报 近日,王女士突发头晕、肢体无力,持续了三天后症状加重,被家人紧急送
医病更医心!“心身同治”助脑梗患者重获健康 今日报 近日,王女士突发头晕、肢体无力,持续了三天后症状加重,被家人紧急送 -
 焦点速递!奔驰商务车七座vito价格 【奔驰商务车七座vito价格】在选择高端商务用车时,奔驰VITO系列凭借其
焦点速递!奔驰商务车七座vito价格 【奔驰商务车七座vito价格】在选择高端商务用车时,奔驰VITO系列凭借其 -
 东兴证券: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42.12%,拟派发现金红利2.46亿元-微速讯 人民财讯8月26日电,8月26日晚,东兴证券发布2025年半年报显示,实现营
东兴证券: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42.12%,拟派发现金红利2.46亿元-微速讯 人民财讯8月26日电,8月26日晚,东兴证券发布2025年半年报显示,实现营 -
 明确了!今晚起,海南油价下调 最新消息!海南油价今晚下调92 汽油8 23元 升95 汽油8 74元 升2025年8
明确了!今晚起,海南油价下调 最新消息!海南油价今晚下调92 汽油8 23元 升95 汽油8 74元 升2025年8 -
 猛玛品牌战略全新升级,四大产品线协同打造“创作者生态”新底座 2025年8月26日,全球无线音视频领域的领军品牌 HOLLYLAND 猛玛成
猛玛品牌战略全新升级,四大产品线协同打造“创作者生态”新底座 2025年8月26日,全球无线音视频领域的领军品牌 HOLLYLAND 猛玛成 -
 世锦赛丨中国女排3:1胜哥伦比亚队 收获两连胜提前晋级16强 人民网北京8月26日电(记者胡雪蓉)北京时间8月25日晚,2025年女排世锦
世锦赛丨中国女排3:1胜哥伦比亚队 收获两连胜提前晋级16强 人民网北京8月26日电(记者胡雪蓉)北京时间8月25日晚,2025年女排世锦 -
 【独家焦点】金博股份(688598.SH)上半年净亏损1.68亿元 格隆汇8月26日丨金博股份(688598 SH)发布中报,2025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
【独家焦点】金博股份(688598.SH)上半年净亏损1.68亿元 格隆汇8月26日丨金博股份(688598 SH)发布中报,2025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 -
 奔驰卡车型号有哪些|热推荐 【奔驰卡车型号有哪些】在汽车市场中,奔驰(Mercedes-Benz)作为豪华
奔驰卡车型号有哪些|热推荐 【奔驰卡车型号有哪些】在汽车市场中,奔驰(Mercedes-Benz)作为豪华 -
 天润云(02167)公布中期业绩 净利润2767.1万元 同比增长98.9% 速看料 智通财经APP讯,天润云(02167)公布2025年中期业绩,收入约2 69亿元,同
天润云(02167)公布中期业绩 净利润2767.1万元 同比增长98.9% 速看料 智通财经APP讯,天润云(02167)公布2025年中期业绩,收入约2 69亿元,同 -
 当前热议!图解财报:南极电商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362.07万元,同比减少82.52% 南极电商发布2025半年度报告显示,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3 53亿元,
当前热议!图解财报:南极电商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362.07万元,同比减少82.52% 南极电商发布2025半年度报告显示,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3 53亿元, -
 焦点!新三板基础层公司万通新材登龙虎榜:当日价格振幅达到160.00% 新三板基础层公司万通新材登龙虎榜:当日价格振幅达到160 00%每经讯,2
焦点!新三板基础层公司万通新材登龙虎榜:当日价格振幅达到160.00% 新三板基础层公司万通新材登龙虎榜:当日价格振幅达到160 00%每经讯,2 -
 新三板创新层公司同步新科登龙虎榜:2025年8月25日至2025年8月26日涨跌幅累计达到-... 每经讯,2025年8月26日,新三板创新层公司同步新科(838129,收盘价:0
新三板创新层公司同步新科登龙虎榜:2025年8月25日至2025年8月26日涨跌幅累计达到-... 每经讯,2025年8月26日,新三板创新层公司同步新科(838129,收盘价:0 -
 亲哥回应全红婵被AI仿声带货:她天天在训练,怎么卖鸡蛋? 亲哥回应全红婵被AI仿声带货:她天天在训练,怎么卖鸡蛋?
亲哥回应全红婵被AI仿声带货:她天天在训练,怎么卖鸡蛋? 亲哥回应全红婵被AI仿声带货:她天天在训练,怎么卖鸡蛋? -
 西媒:维尼修斯不肯现在续约!皇马不会被要挟,不续约就明年卖他_热文 西媒:维尼修斯不肯现在续约!皇马不会被要挟,不续约就明年卖他,西媒,
西媒:维尼修斯不肯现在续约!皇马不会被要挟,不续约就明年卖他_热文 西媒:维尼修斯不肯现在续约!皇马不会被要挟,不续约就明年卖他,西媒, -
 持续推进“AI智能体”平台 尚品宅配上半年净利润同比改善-快播报 本报讯(记者李雯珊)8月26日,广州尚品宅配(300616)家居股份有限公
持续推进“AI智能体”平台 尚品宅配上半年净利润同比改善-快播报 本报讯(记者李雯珊)8月26日,广州尚品宅配(300616)家居股份有限公 -
 【时快讯】智能坐便器能效水效标准更新升级 记者8月26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,市场监管总局(国家标准委)近日发布
【时快讯】智能坐便器能效水效标准更新升级 记者8月26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,市场监管总局(国家标准委)近日发布 -
 热消息:千城百县看中国|山东沂南:软枣猕猴桃巧变乡村振兴“致富果” 近日,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马牧池乡软枣猕猴桃迎来丰收季。一串串翠
热消息:千城百县看中国|山东沂南:软枣猕猴桃巧变乡村振兴“致富果” 近日,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马牧池乡软枣猕猴桃迎来丰收季。一串串翠 -
 快看点丨江西婺源:悬崖小村迎来“晒秋季” 当下,江西省婺源县篁岭村晒秋景象色彩艳丽。谷物与辣椒交相辉映,
快看点丨江西婺源:悬崖小村迎来“晒秋季” 当下,江西省婺源县篁岭村晒秋景象色彩艳丽。谷物与辣椒交相辉映, -
 山西蒲县:开展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守护绿色“活化石 山西省临汾市蒲县现存的名木多为树龄悠久、形态独特的珍稀树种,它
山西蒲县:开展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守护绿色“活化石 山西省临汾市蒲县现存的名木多为树龄悠久、形态独特的珍稀树种,它 -
 江西婺源:悬崖小村迎来“晒秋季”-最新资讯 当下,江西省婺源县篁岭村晒秋景象色彩艳丽。谷物与辣椒交相辉映,
江西婺源:悬崖小村迎来“晒秋季”-最新资讯 当下,江西省婺源县篁岭村晒秋景象色彩艳丽。谷物与辣椒交相辉映,
热门资讯
-
 猛玛品牌战略全新升级,四大产品线协同打造“创作者生态”新底座 2025年8月26日,全球无线音视频领...
猛玛品牌战略全新升级,四大产品线协同打造“创作者生态”新底座 2025年8月26日,全球无线音视频领... 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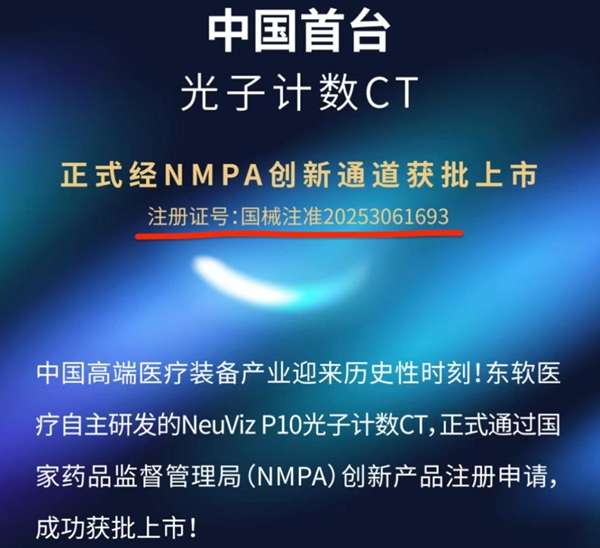 东软联影同日报捷,光子计数CT“首台”身份扑朔迷离 日前,东软医疗与联影医疗同日官宣...
东软联影同日报捷,光子计数CT“首台”身份扑朔迷离 日前,东软医疗与联影医疗同日官宣... -
 获奖者说:与贵州百灵同行,我的苗药创意探索之路 贵州百灵2025学院奖创意大赛圆满落...
获奖者说:与贵州百灵同行,我的苗药创意探索之路 贵州百灵2025学院奖创意大赛圆满落... -
 东软以光子计数CT技术赋能精准医疗,打造超高清、低剂量诊疗新范式 近日,中国高端医疗装备产业迎来历...
东软以光子计数CT技术赋能精准医疗,打造超高清、低剂量诊疗新范式 近日,中国高端医疗装备产业迎来历...
观察
图片新闻
-
 中国宏桥(01378.HK)8月26日耗资5007.71万港元回购203.4万股|即时焦点 格隆汇8月27日丨中国宏桥(01378 H...
中国宏桥(01378.HK)8月26日耗资5007.71万港元回购203.4万股|即时焦点 格隆汇8月27日丨中国宏桥(01378 H... -
 当前热讯:经纬线·国旗的尊严 由我们捍卫 一面国旗,他扛在肩上,用青春守护...
当前热讯:经纬线·国旗的尊严 由我们捍卫 一面国旗,他扛在肩上,用青春守护... -
 通讯!三亚这群消防员台风天彻夜奋战 8月26日,蔡扬驰(前)和队友在三亚...
通讯!三亚这群消防员台风天彻夜奋战 8月26日,蔡扬驰(前)和队友在三亚... -
 焦点速递!记者:德科与马略卡高层会面,商讨福特等多名球员的未来 记者:德科与马略卡高层会面,商讨...
焦点速递!记者:德科与马略卡高层会面,商讨福特等多名球员的未来 记者:德科与马略卡高层会面,商讨...
精彩新闻
-
 奔驰大g一般指的哪款车 观热点 【奔驰大g一般指的哪款车】“奔驰...
奔驰大g一般指的哪款车 观热点 【奔驰大g一般指的哪款车】“奔驰... -
 焦点要闻:公益圈 | 应急知识你问我答:遇到暴雨洪水不要慌!   新华公益原创IP栏目《...
焦点要闻:公益圈 | 应急知识你问我答:遇到暴雨洪水不要慌!   新华公益原创IP栏目《... -
 快讯:三亚用艺术让游客的脚步停留 三亚新闻网8月26日消息(三亚传媒...
快讯:三亚用艺术让游客的脚步停留 三亚新闻网8月26日消息(三亚传媒... -
 2025年全国“敬老月”活动将于10月开展 焦点观察 记者19日从民政部获悉,全国老龄工...
2025年全国“敬老月”活动将于10月开展 焦点观察 记者19日从民政部获悉,全国老龄工... -
 韩国购买100多架波音飞机 韩国购买100多架波音飞机,韩国,波...
韩国购买100多架波音飞机 韩国购买100多架波音飞机,韩国,波... -
 为困难家庭孩子点亮多彩假期 为困难家庭孩子点亮多彩假期
为困难家庭孩子点亮多彩假期 为困难家庭孩子点亮多彩假期 -
 焦点资讯:中国首部8K拍摄太空电影《窗外是蓝星》预售开启! 想沉浸式体验穿越云层、抵达太空吗...
焦点资讯:中国首部8K拍摄太空电影《窗外是蓝星》预售开启! 想沉浸式体验穿越云层、抵达太空吗... -
 当前信息:安通控股今日大宗交易平价成交7000万股,成交额2.52亿元 8月26日,安通控股大宗交易成交700...
当前信息:安通控股今日大宗交易平价成交7000万股,成交额2.52亿元 8月26日,安通控股大宗交易成交700... -
 奔驰v8跑车多少钱一辆 【奔驰v8跑车多少钱一辆】在汽车市...
奔驰v8跑车多少钱一辆 【奔驰v8跑车多少钱一辆】在汽车市... 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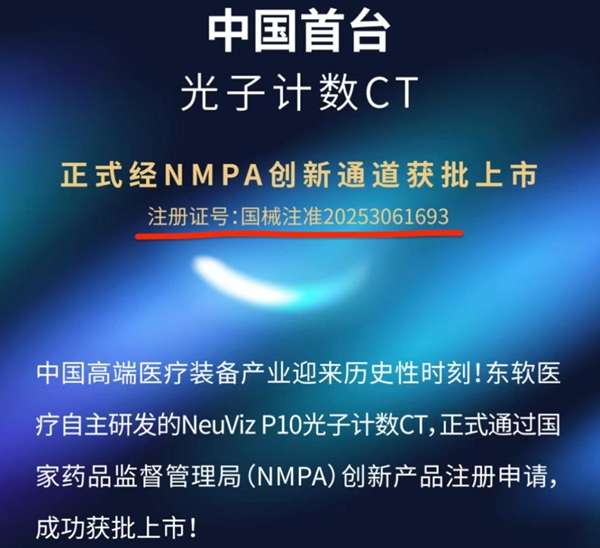 东软联影同日报捷,光子计数CT“首台”身份扑朔迷离 日前,东软医疗与联影医疗同日官宣...
东软联影同日报捷,光子计数CT“首台”身份扑朔迷离 日前,东软医疗与联影医疗同日官宣... -
 前沿热点:全国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8月25日8时至26日8时,受降雨影响...
前沿热点:全国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8月25日8时至26日8时,受降雨影响... -
 每日看点!前7个月中国与阿盟贸易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中新社北京8月26日电(记者尹倩芸)...
每日看点!前7个月中国与阿盟贸易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中新社北京8月26日电(记者尹倩芸)... -
 每日快看:航天动力:公司业务布局明确围绕“四板块一核心”展开 同花顺(300033)金融研究中心08月...
每日快看:航天动力:公司业务布局明确围绕“四板块一核心”展开 同花顺(300033)金融研究中心08月... -
 每日报道:【地评线】桂声网评:山水之外有 “情绪”——广西文旅用体验感留住游客心 “穿着救生衣躺在河里看云卷云舒,...
每日报道:【地评线】桂声网评:山水之外有 “情绪”——广西文旅用体验感留住游客心 “穿着救生衣躺在河里看云卷云舒,... -
 锌商品报价动态(2025-08-26) 交易商品牌 产地交货地最新报价锌...
锌商品报价动态(2025-08-26) 交易商品牌 产地交货地最新报价锌... -
 奔驰s400启动步骤如下 【奔驰s400启动步骤如下】对于初次...
奔驰s400启动步骤如下 【奔驰s400启动步骤如下】对于初次... -
 电气风电(688660)龙虎榜数据(08-26) 每日观点 交易所2025年8月26日公布的交易公...
电气风电(688660)龙虎榜数据(08-26) 每日观点 交易所2025年8月26日公布的交易公... -
 日经、朝日加入读卖行列:Perplexity AI 现遭日本三大媒体起诉 日经、朝日加入读卖行列:Perplexi...
日经、朝日加入读卖行列:Perplexity AI 现遭日本三大媒体起诉 日经、朝日加入读卖行列:Perplexi... -
 欧股集体低开 欧洲斯托克50指数开盘跌0.9% 人民财讯8月26日电,欧股集体低开...
欧股集体低开 欧洲斯托克50指数开盘跌0.9% 人民财讯8月26日电,欧股集体低开... -
 每日速看!济阳街道南门社区开展“文明餐桌践于行”专项宣传行动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...
每日速看!济阳街道南门社区开展“文明餐桌践于行”专项宣传行动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... -
 奔驰r500的售价是多少 当前资讯 【奔驰r500的售价是多少】奔驰R500...
奔驰r500的售价是多少 当前资讯 【奔驰r500的售价是多少】奔驰R500... -
 生意社:8月26日 昆明地区金属硅441#价格行情 视点 8月26日,国内昆明地区金属硅411 ...
生意社:8月26日 昆明地区金属硅441#价格行情 视点 8月26日,国内昆明地区金属硅411 ... -
 A500ETF易方达(159361)盘中净申购达4800万份,机构称核心资产情绪指标呈乐观趋势|今日热闻 市场今日午后延续震荡,盘面上,养...
A500ETF易方达(159361)盘中净申购达4800万份,机构称核心资产情绪指标呈乐观趋势|今日热闻 市场今日午后延续震荡,盘面上,养... -
 【独家焦点】小摩:升洛阳钼业目标价至13.5港元 维持“增持”评级 小摩:升洛阳钼业目标价至13 5港...
【独家焦点】小摩:升洛阳钼业目标价至13.5港元 维持“增持”评级 小摩:升洛阳钼业目标价至13 5港... -
 每日视讯:主力板块资金流入前10:光学光电子流入10.73亿元、游戏流入10.30亿元 【主力板块资金流入前10:光学光电...
每日视讯:主力板块资金流入前10:光学光电子流入10.73亿元、游戏流入10.30亿元 【主力板块资金流入前10:光学光电... -
 我国自主研制超大型耙吸挖泥船将下水 观察 经过3年多研制,今天(8月26日)中午...
我国自主研制超大型耙吸挖泥船将下水 观察 经过3年多研制,今天(8月26日)中午... -
 微头条丨奔驰gls200怎么样 【奔驰gls200怎么样】作为梅赛德斯...
微头条丨奔驰gls200怎么样 【奔驰gls200怎么样】作为梅赛德斯... -
 日经225指数收盘跌0.97% 韩国综合指数跌0.95% 视焦点讯 8月26日,日韩股市收盘齐跌。日经2...
日经225指数收盘跌0.97% 韩国综合指数跌0.95% 视焦点讯 8月26日,日韩股市收盘齐跌。日经2... -
 获奖者说:与贵州百灵同行,我的苗药创意探索之路 贵州百灵2025学院奖创意大赛圆满落...
获奖者说:与贵州百灵同行,我的苗药创意探索之路 贵州百灵2025学院奖创意大赛圆满落... -
 育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...
育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... -
 新动态:天工开物·数字艺术暨“沄影”数字文旅专题发布会在京发布  8月22日,由沄影主办、新华...
新动态:天工开物·数字艺术暨“沄影”数字文旅专题发布会在京发布  8月22日,由沄影主办、新华... -
 何小鹏称自己是特斯拉中国首批车主,雷军曾劝他不要造车 焦点速看 何小鹏称自己是特斯拉中国首批车主...
何小鹏称自己是特斯拉中国首批车主,雷军曾劝他不要造车 焦点速看 何小鹏称自己是特斯拉中国首批车主... -
 多部门出招!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迎“暖心升级”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19日发布的...
多部门出招!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迎“暖心升级”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19日发布的... -
 杭州桐庐:“漂流热”激活乡村“清凉经济” 上午,位于杭州市桐庐县合村乡的雅...
杭州桐庐:“漂流热”激活乡村“清凉经济” 上午,位于杭州市桐庐县合村乡的雅... -
2025全国青少年信息素养大赛总决赛在浙江桐乡举办 焦点信息   新华社照片,桐乡(浙...
-
 杭州桐庐:“漂流热”激活乡村“清凉经济”-今日讯 上午,位于杭州市桐庐县合村乡的雅...
杭州桐庐:“漂流热”激活乡村“清凉经济”-今日讯 上午,位于杭州市桐庐县合村乡的雅... -
 生意社:8月26日山东金生润化工小苏打价格暂稳 8月26日山东金生润化工小苏打价格...
生意社:8月26日山东金生润化工小苏打价格暂稳 8月26日山东金生润化工小苏打价格... -
 焦点关注:济宁移动圆满完成“儒韵消夏 畅游济宁”首届福特烈马创造营音乐派对通... 鲁网8月26日讯近日,“儒韵消夏畅...
焦点关注:济宁移动圆满完成“儒韵消夏 畅游济宁”首届福特烈马创造营音乐派对通... 鲁网8月26日讯近日,“儒韵消夏畅... -
关注:2025全国青少年信息素养大赛总决赛在浙江桐乡举办   新华社照片,桐乡(浙...
-
 精彩看点:决胜“十四五” 打好收官战|深化养老服务改革,推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 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,是实施积极...
精彩看点:决胜“十四五” 打好收官战|深化养老服务改革,推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 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,是实施积极... -
 “雷锋故里”出新招 暑期“官方带娃”受欢迎 明年暑假我还想参加托管!8月22日...
“雷锋故里”出新招 暑期“官方带娃”受欢迎 明年暑假我还想参加托管!8月22日... -
 记者手记:在瘢痕里长出“他们的光”_每日看点 4岁女孩小宇(化名)低头拽了拽帽...
记者手记:在瘢痕里长出“他们的光”_每日看点 4岁女孩小宇(化名)低头拽了拽帽... -
 云南罗平:文体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8月23日,2025年罗平板桥喀斯特山...
云南罗平:文体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8月23日,2025年罗平板桥喀斯特山... -
 东软以光子计数CT技术赋能精准医疗,打造超高清、低剂量诊疗新范式 近日,中国高端医疗装备产业迎来历...
东软以光子计数CT技术赋能精准医疗,打造超高清、低剂量诊疗新范式 近日,中国高端医疗装备产业迎来历... -
 今日热搜:奔驰gl500多少钱一辆 【奔驰gl500多少钱一辆】作为梅赛...
今日热搜:奔驰gl500多少钱一辆 【奔驰gl500多少钱一辆】作为梅赛... -
 海南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 全力防御台风“剑鱼” 动态焦点 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24日10...
海南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 全力防御台风“剑鱼” 动态焦点 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24日10... -
 新消息丨3129元买机票后发现另一平台仅售570元 近日,消费者黄先生反映称,2024年...
新消息丨3129元买机票后发现另一平台仅售570元 近日,消费者黄先生反映称,2024年... -
 记者手记:在瘢痕里长出“他们的光”-热点 4岁女孩小宇(化名)低头拽了拽帽...
记者手记:在瘢痕里长出“他们的光”-热点 4岁女孩小宇(化名)低头拽了拽帽... -
 第九个残疾预防日宣传聚焦预防伤害致残 8月25日是全国第九个残疾预防日。...
第九个残疾预防日宣传聚焦预防伤害致残 8月25日是全国第九个残疾预防日。... -
 新华日用消费周报|上半年规上轻工企业营收超11万亿元;广州立白(番禺)有限公司...  本周(8月11日—8月15日),...
新华日用消费周报|上半年规上轻工企业营收超11万亿元;广州立白(番禺)有限公司...  本周(8月11日—8月15日),...